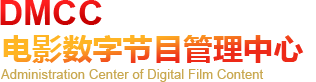曹保平在《烈日灼心》的前半部分表现他对西部片风格的强烈钟爱,直到邓超与段奕宏的猫鼠游戏开始吊起观众胃口的时候,电影的西部片风格才逐渐褪去,把一个鲜明的中国故事呈现了出来。
邓超、段奕宏和郭涛饰演的角色,在年轻时为什么会卷入一场灭门案?电影最后给出的解释是,他们是被另外一个真正动手的罪犯胁迫的。这个解释有些牵强,因为毕竟是三对一,他们年轻时若是真善良,完全有能力阻止这场灭门案。一个行得通的解释是,他们内心本来就有恶。
邓超在逃离作案现场后坚持要求回去,带走未被灭口的初生婴儿,是善浮上来的时候。恶是本能,是可以被血腥、恐惧所激发出来的;善也是本能,与恶一样更容易被激发。从这一刻起,三个参与作恶的年轻人,就注定一辈子活在自我谴责中。
自我谴责是种宝贵的情感,它包含着反思与忏悔,这种在当下很难真切体会到的品质。观众感慨《烈日灼心》的故事,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对现在环境的对照。如果电影刺激不到观众联想现实,那么就会失去它的现实意义,在这一点上,《烈日灼心》做得很好。
《烈日灼心》当然是在写人性,整部电影都那么直白地把人性展览于银幕之上,能说它不是写人性吗。只是它在写人性复杂一面的时候,好在没用曲笔,电影用非常简单的方式告诉观众:看看吧,人性就是这样,它既矛盾又复杂,善恶纠缠,爱恨交织,主导人性走向的既有环境因素,也有社会因素,更有内心因素。真实的人在内心动力的驱使下,可以做出匪夷所思的事情。
《烈日灼心》的故事核心很硬,这是一个讲述三个杀人犯如何爱一个被他们杀死了全部亲人的女孩的故事。这个故事核心经得起各个角度的揣摩,可以延伸出多种戏剧关系。曹保平并没有把重点放在赎罪主题上,电影对于赎罪这个词,只是轻描淡写了一下,而更多地把笔触引向了“爱”。三个杀人犯因为“爱”,可以为他们的“女儿”作出任何牺牲,因此他们愈是爱之切,故事的戏剧性就愈加强烈,观众内心的滋味也愈加复杂,电影在此刻就对观众形成了“绑架”效应,你要一起参与判定:要不要原谅这三个年轻时曾犯过错误的人?
故事也试图为观众原谅他们提供理论与事实依据。主犯不是他们,女孩的母亲是在被侵犯的过程中犯心脏病而死,邓超在当辅警的过程中屡次立功,郭涛也变成了一个抓抢劫犯的好出租车司机……他们对自己不是主犯的这个事实守口如瓶,这种只求一死的决心,也为观众原谅他们提供了巨大的情感动力。电影这么处理是有道理的,这也是为什么电影在看的过程中会紧张而压抑,但在看完会觉得放松。因为电影给了人以希望,它是一部让坏人看了变好、好人看了之后变得更好的电影,它是在给处在困境中的人提供一个出路。